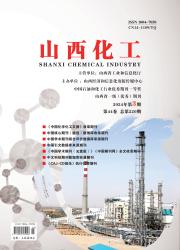
《山西化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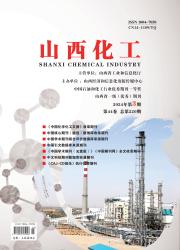
2017 年12 月,光明日报曾发表一篇文章,名为“新时代中国非遗的文化使命”。文中说到“非遗的多样功能决定其具有历史、文化、精神、科学、审美、和谐、教育和经济等多方面价值,价值积累形成文脉,以非遗文化形态呈现。”非遗作为载道的文化,凝结于中华传统文脉,同时也呈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有序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传统文化置于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的坐标系,更视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它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和骨气。由此可见,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任重而道远。所谓的非遗,是指在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于无形之中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积淀与文化内涵,它在潜移默化地传递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俗话说5000 年文明看山西,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然少不了繁荣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资源。本文就以山西地区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来探析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
一、现量性
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类别上,既有声乐、又有器乐;既有独奏独唱,又有合奏,是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人们根据对音乐的需求所创设和传承的音乐艺术形式,它作为人的精神产物被创造出来,集中的体现着人的精神品格。在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中,音乐类非遗具有和其他遗产类型明显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其自身的即时互动性,也就是王夫之“现量”,感性直观和瞬间直觉获得的东西,强调现在、当下的感受,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1]从音乐活动的角度看,“现量”的三层涵义“现在”、“现成”、“显现真实”,分别是在表演过程中,表演者与受众之间存在当场、当下就发生的艺术传递、反馈、接受等,非常强调音乐表演者和受众之间的亲身经历、体验的情境,比如五台山佛教仪式音乐,单凭文字或别人口述,没有亲身体验,将自己置身其内,就无法感受到庄重和洗礼,无法引起强烈的审美反映,无法感受中国佛教音乐的审美情趣与儒家、道家相渗透、融合共同趋于“和、静、清、远、古、淡”之感。而传统美术、制造工艺类会产生一个静态凝固、可感、可触的作品,无论受众在什么时候欣赏都可以,不需要我们在艺术传达过程中去欣赏、去体会。而音乐并非表演者的自娱自乐,需要欣赏者在直觉的基础上,重视音乐刹那瞬间的震撼与感动,重视观众与音乐作品浑然一体的直接感发,然后调动再创造的想象力和联想力,激起丰富的情感,深深的被音乐所吸引,所感动,与表演者接通。
二、高度依赖性
音乐类非遗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对受众的高度依赖性。任何文化都必须依赖社会群体,才能生存或兴盛,只是音乐类更受众的依赖要远远高于其他类型,受众决定了音乐、乐种的生死存亡。例如:晋南威风锣鼓,虽然时代变迁,民俗活动也随之发生变化,但人与天同庆,完美崇高的精神保留下来,广大民众依然强烈认同,主要是源于锣鼓参与了民间礼俗的仪式性意义,符合受众群体固定的审美与文化。
又如山西戏曲,很多剧团无法生存,濒临灭绝,因缺少观众导致演出场次骤降而解散,仅仅靠政府的“输血”达不到自救,所以受众是音乐类非遗的生存基础。
三、不确定性
传统音乐类的生存特征还表现在不确定性,虽然表演类非遗也有文本、历史记录,但我们仅仅通过这些文本类资料对它欣赏,基本上体会不到美感或者很肤浅,并且演奏过程伴随着曲终就结束消失了,难以留存,尽管现代科技手段对表演类非遗进行了数字保存,但在演奏过程中,所涉及的表演者与欣赏者的生理和心理现象等内在规律及其复杂,难以精确量化,这是音乐类有别于工艺美术、民间口传类最根本的区别。例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泽州四弦书,在表演过程中并非是根据乐谱绝对符合原创作者的意思,而是在每次的表演中都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二度创作”,因为演奏者作为表演主体,他的民族、时代、个人修养与背景,使得他理解作品与表现作品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形成了不同的琴家流派,再加上我国传统音乐的记谱法为简略的骨干音记谱,谱简腔繁,很多时候表现出即兴性,谱面与实际演奏效果表现较大出入,须进行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才能得到“真传”,个人色彩明显。所以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个人生理、心理因素影响很大,其中的规律难以捉摸。不似书法、绘画等其他的非遗种类,可以呈现可感、可见的有形作品,即使没有口传心授,通过日积月累,刻苦临摹也可以掌握创作手法达到精通。而音乐类的非遗往往会涉及到很多抽象、不可触摸、不可见的声音等感性形态,难以保存且变化万千,比如民歌,其是劳动人民口耳相传集体创作的民间音乐,经常没有文字记谱,带有即兴性,即使是同一个民歌手在不同时期演唱同一首曲调时,往往也有不同的变化与领悟。
上一篇:新时期山西农村题材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建构以电
下一篇:没有了